
释太虚 (1890.1.8-1947.3.17),法名唯心,字太虚,号昧庵,俗姓吕,乳名淦森,学名沛林,属牛,出生在清代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,在上海玉佛寺示寂于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,原籍浙江崇德(今浙江桐乡),生于浙江海宁,近代著名高僧。

太虚大师提倡“人生佛教”的根本宗旨是在于:以大乘佛教“舍己利人”、“饶益有情”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,建立完善的人格、僧格。他常说:“末法期佛教之主潮,必在密切人间生活,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,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”。因此,他提出了“即人成佛”、“人圆佛即成”等口号。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,偈曰:“仰止唯佛陀,完成在人格,人圆佛即成,是名真现实”(《成人》)。

真切的禅悟经验,对全体佛学的宏观把握,使太虚大师对禅宗怀有深厚感情,给予高度评价,他在文中多次高推禅宗为中国佛学乃至全体佛法的骨髓、核心。如1928年10月在巴黎东方博物院的讲词《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》中,他自豪地赞叹:
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性,以达摩西来的启发,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,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,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,佛心与自心印合无间。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的、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,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,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,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及宋明理学。
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,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。……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,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,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,使世人各个直证佛陀的心境。

《在黄梅讲演之记载》说中国自晚唐、五代以来之佛教,“可谓完全是禅宗之佛教,禅风之所播,不惟遍及佛教各宗,且儒家宋明理学、道家之性命双修,亦无不受禅宗之酝酿而成者。故禅宗者,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。”
《佛教各宗派源流》说:到宋初,“禅宗之风风靡全国,不独佛教之各宗派皆依以存立,即儒道二家亦潜以禅为底骨”。《对中国禅宗的感想》说中国自唐宋以来佛法之骨髓胥在于禅宗,研究教理、修习止观,及念诵、拜祷等等法门虽然很多,“直究根源,皆摄在禅宗,所以宋元以来通常流行之天台或贤首等,其向上之人,自行仍是禅宗。”
认为中观、唯识、天台、华严等教理的作用,主要在于说服人信仰佛教,谈到修证,台、贤、唯识等教宗皆不得力,实际上只有禅、净二宗切实可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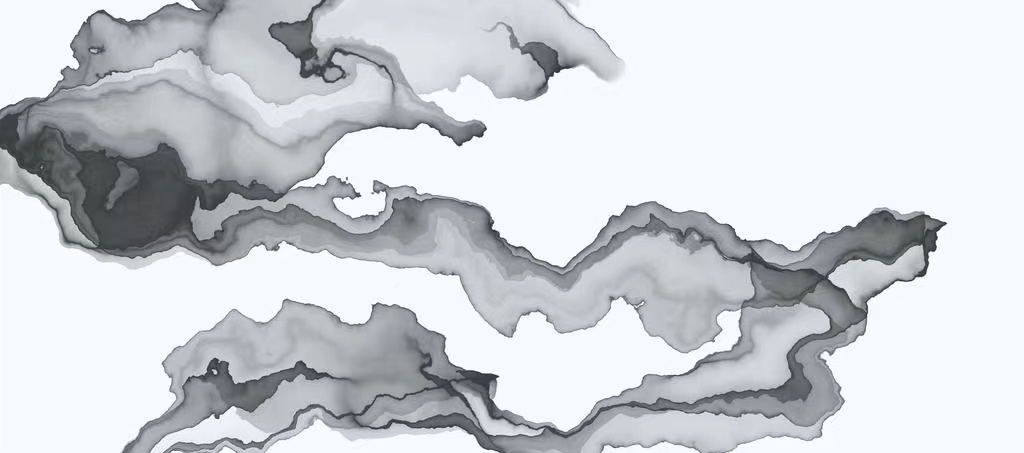
《天台四教义与中国佛学》(1942)一文中说:
禅宗既重实践修持,中国佛教历史开始后,重禅的精神都收归此宗;所以唐宋以来,它能体表兴盛,成为中国佛教的正统。
1943讲于汉藏教理院的《中国佛学》总结说:南洋佛教的特质在律仪,藏传佛教的特质在密咒,日本佛教的特质在于闻慧及通俗应用,“从以上各地特质比较起来,反显出中国汉地佛教特质在禅”,“中国佛法之骨髓,在于禅。” 台、贤二宗之学,由先得禅定而后印以经论,才建立为宗,其初祖多分为禅师,若第二第三代祖师不向教理方面发展,则其学必归于禅宗。

中国佛教的禅,可归纳为从“依教修心禅”(安般禅、五门禅、念佛禅、实相禅)、“悟心成佛禅”(达摩至六祖禅)、“超佛祖师禅”(行思、怀让至夹山等)、“越祖分灯禅”(五宗)、宋元明清禅五大阶段,宋元明清禅又包括公案之拈颂、话头之疑参、禅净之合修、宗教之合会、空默之观照、语录之纂研、坐跑之兼运、僧俗之常套、仙道之傍附、儒理之推演等内容。中国佛教初期由道安奠定的主流,有本佛、重经、博约、重行四大特点,虽受旁流影响,而主流迄今未变,禅宗即属于此系。
《佛教各宗派源流》、《佛乘宗要论》等文中,总结唐末以来禅宗独盛之原因有三点:
1、唐武宗灭佛之后,诸宗皆衰,唯禅宗“专务清简,不必寺宇,不须经典,不拘仪制,不须器物,不重像设”,又农禅并举,躬耕山林以自供衣食,故独得发展。
2、惟独禅宗,用通俗化的语录及诗文以播其化,“既平易近人,又裕兴味,传之自能扩充。
3、小乘教义多从反外道而立,大乘教义多从反外小而立,此土本无外道、小乘之心理思想为基础,颇不易得解;天台、贤首二宗虽融通变化,仍未脱印度佛学之巢臼。惟独禅宗,“竟全脱经律等羁绊,间借用儒道二家之言以利化导,对于第一义谛,则唯引人之钻究自悟,而与人言者,不过朴素之平常话,而与国人之心习邻近,人喜相就,则易发达”。“禅宗不讲经论深微奥妙之义理,但求悟得本来真心,即悟得亦无详实之说明,间有一二简单表示,亦不离通俗之言行,此则最合中国人向来之心理。”

这三点,说得可谓客观。禅宗所以能在唐末以后发达的原因,也正是禅宗的优良传统所在。禅宗将释迦教法之精髓浓缩为简易活泼的履践之道、生活艺术,最具有中国风格因而最适应中土文化,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,不远推于他生后世,不依傍神佛,从“众生与佛同此一心,依佛法修证,皆可成佛”的确信出发,力图在今世乃至当念发明自心本具的佛性,其修持,“不过平平实实发明此心,并不是什么秘密巧怪法门”, “仅令人自得其心之与佛与众生所同然者,自肯自信,别无他种奇妙玄奥之义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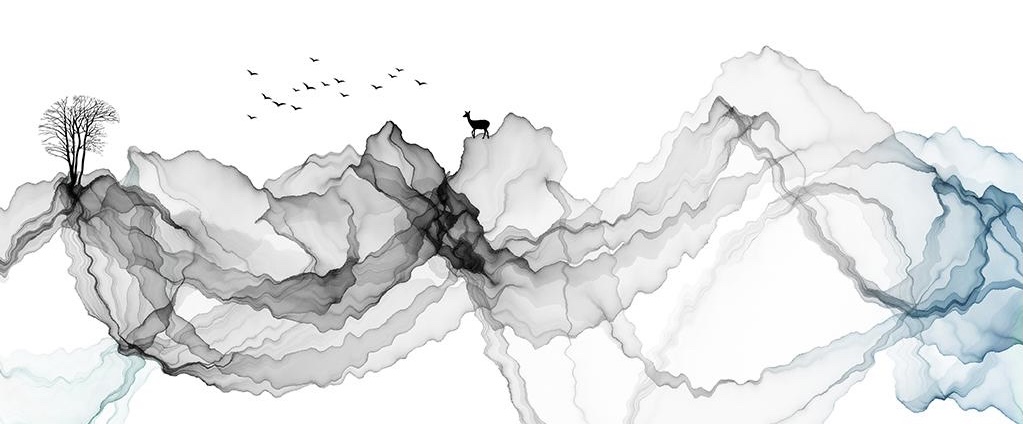
最能体现释迦牟尼以如实知见的智慧自净其心而得解脱的佛法心髓,最能体现人间佛教尊重人、注重人生现实、由人而佛的精神。
禅宗强调“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间觉”,打破了宗教修行与世俗生活、做人与成佛、出世与入世、出家与在家等隔碍,并有随方解缚、活泼机用、农禅并举等诸多优良传统,最容易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势人心而应机施教、变革自身,最符合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精神。

禅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民族思想文化、道德精神的建设者,是因为开创者六祖惠能大师有大革命的精神。大师《唐代禅宗与现代思潮》(1920)一文,将禅宗与学术思潮、社会思潮比较,指出宗门于教主、经典、戒律、形仪等方面,皆有反信教的学术精神:禅宗不同多数宗教以崇拜教主为立教之本,而“反溯未有牟尼、未有佛陀之前,彻底掀翻,和盘拆卸。如何是佛?曰:干屎橛。”德山宣鉴禅师等乃并佛与祖同时呵骂之。
禅宗初离经论,后来禁止记录禅语,“后复有人以三藏经教、诸祖言语,同遮拨为拭脓疮之烂纸者,直令人人胸头不挂留佛教祖典一个字脚。”禅宗不死板拘守印度教制,戒律载舍利弗以耕治田园、种谷植树为“下口邪命食”,而唐代宗门诸德,则多刀耕火种,自食其力,不受形制仪状之拘束,惟贵称性发舒之德行。
总之,禅宗具有科学的、哲学的、艺术的、道术的精神及反玄学的实用精神、反理论的直觉精神、反因袭的创化精神、全体融美的精神、自性尊圆的精神。禅宗最富科学精神而为科学家所望尘莫及者,在于须各人自己从实验上发见自心佛性,“却又能恒保此科学之精神而不堕入科学之形式,致由实验归纳重走入推理演绎之迷路,此诚现代科学所由发达之源也。”

因此,太虚大师高推禅宗为佛学之核心、中国佛学之骨髓,并满怀民族自信感地说:
惟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,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,现今惟在于中国。
强调中国佛教的复兴,不能离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,不能离了这个传统的骨髓——禅宗。在《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》(1926)中,太虚大师指出:
中华佛法,实以禅宗为骨子。禅衰而趋乎净,虽若有江河日下之概,但中华之佛教,如能复兴也,必不在于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识,而仍在乎禅。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,中华各宗教之佛法,皆籍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。
并表明,他多年来折中于法相唯识学,以整理大小乘内教及东西洋之外学,“仅为顺机宏化之一方,而旨归之所存,仍在禅、净。”

大师指出:作为弘扬佛法的法师,须得参禅开悟,“握得宗门真旨,方足以阐明教理,及行佛事而施佛化。” 《佛法导言》中强调:若自发心求悟入大乘者,必入宗门;其真悟大乘者,亦未有不契宗门。参禅开悟得入祖位,方能弘扬大乘,否则自缚未解,不能解人缚。
讲经说论、修习教观,只能令人得人天权小之益及种大乘善根,不入大乘。若非已悟向上事,纵讲习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等,亦同贪着戏论,犹如用虾为目,隔靴搔痒,只是假名大乘人。故必令真参实悟,自明本来,佛亦不求,乃入大乘之正轨。
按大师的思路,他所说“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,使人类进步、世界改善”的人间佛教之建设,应以禅宗的振兴为关键。他在黄梅的讲演中说:
但中国之佛教,乃禅宗之佛教也,非由禅宗入手,不能奏改善世道之效。

然中国禅宗,早已衰落,大师对此感叹万分,他在《唐代禅宗与现代思潮》中慨叹:禅宗自宋元明清,“随中国全社会而递代降落,亦因人多流杂,法密伪增,浇漓坠堕及今,通身红烂,卧向荆棘林中,殆无复挽狂澜于既倒之望。”《对中国禅宗的感想》说:
然中国禅宗在各丛林,降至今日,虽尚有形式犹具者,而精神则已非矣!求其能握得宗门真旨者,实渺不可得!
《为汉地堪布翻案》(1942)一文中甚至说:“现在真能代表禅宗的善知识,已不可得,故中国无禅宗”。
由于禅宗的衰颓,使人们对汉传佛教失去信心,乃有向南洋、日本、西藏外求的风气,时至今日,复归于南传佛教及拜求藏传佛教,蔚成更大潮流。大师感慨国人之热衷藏密,指出“三昧水”、“梁皇”、“净土”、“大悲”等忏,与诵经、念佛、施食等各种仪轨,本为禅宗济世利生之方便法门,“理义精深,观想详尽,感应道交,时著灵验,应与藏地喇嘛所修各种念诵仪轨事同一例。
而末流疲懈,致沦鄙弃,然而要求者仍在要求”,于是藏密出而代之。此皆因禅宗不振,致僧伽沦散而不为人尊信,“若能复兴禅宗之精神力量,以贯彻于各种应俗之教化,务令求者作者皆激发精诚以赴之,则禅门之念诵经忏安见不如喇嘛耶?”

大师颇以振兴禅宗为己任。1922年,他住持沩山时,接续早已绝嗣的沩仰宗,“辞谢临济五房,决复沩仰一脉”,续32字,自己上接资福真邃为第六世。他对虚云和尚复兴禅宗祖庭南华寺等予以赞叹。1925年11月,他在日本临济大学的讲演中,以临济宗传人自居,自称“太虚虽无临济老汉之手段,然亦欲上追遗规,下振群聋。盖佛法之真髓,厥惟禅宗,临济宗为禅宗正统。”他对禅宗的复兴充满信心,在《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》中说:
默察中华佛法将来之形势,禅宗内感衰弱之隐痛,外受密术之逼拶,旁得法相唯识研究之结果,欲求实证乎离言法性,则禅宗之复振,殆为必然之趋势!



